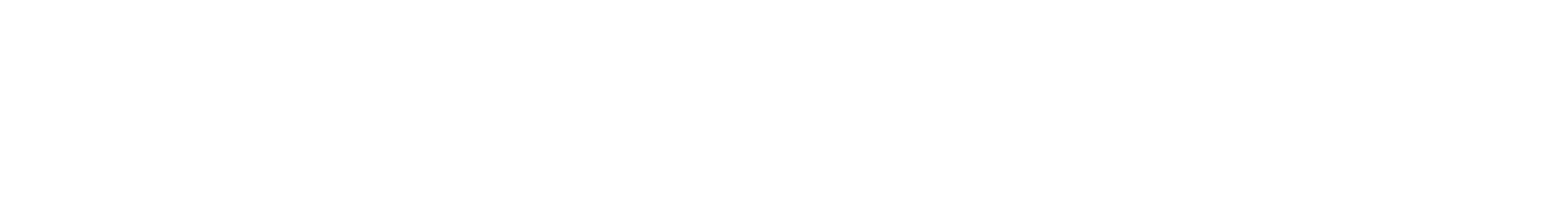Issue 311 Cover Story 从海边女孩到酒店与教育创业家:她的芭堤雅故事 --专访泰国芭堤雅Lovell International School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Cape Dara Resort 副董事长以及Instill Agency 董事总经理 Pattamon Mekavarakul (Beau) 女士
Issue 311 Cover Story
从海边女孩到酒店与教育创业家:她的芭堤雅故事
--专访泰国芭堤雅Lovell International School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Cape Dara Resort 副董事长以及Instill Agency 董事总经理 Pattamon Mekavarakul (Beau) 女士
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与价值。对某些人而言,这条道路或许从童年的梦想开始,也可能因家庭环境、教育经历而逐渐清晰。本期专访的主人公便是一位在酒店与教育两大领域都展现卓越才能的女性——她的故事不仅关乎事业开拓,也折射出当下泰国社会中年轻一代如何平衡传统、现代与全球化视野的现实样貌。

她从芭提雅的海边成长,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11岁便坚持参加新西兰夏令营,随后赴澳洲学习酒店管理。回到泰国,她将所学知识与家族酒店事业结合,推动酒店从传统运营向国际化、专业化发展,并在COVID-19疫情冲击下,以创新思路维系客户与品牌影响力。这一切不仅展示了个人的成长,也反映出泰国旅游与服务产业正面临现代化、国际化与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与机遇。
与此同时,作为母亲与教育实践者,她创办了国际学校Lovell,将心理学与先进教育理念融入课程,注重儿童成长的个性化与多元发展。在泰国社会日益重视教育质量、国际视野与心理健康的背景下,她的教育理念不仅为孩子提供了全方位成长的环境,也为家庭与社会带来积极启示。
.webp)
从酒店管理到教育创新,她的经历勾勒出一幅跨界、成长与社会价值交织的画面。这不仅是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的故事,更是一堂关于如何在多重身份中找到平衡、如何用热情与智慧影响他人生活的生动课程,也折射出泰国社会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与趋势。
本期专访,我们将带领读者走近她的成长轨迹、职业实践与教育理念,探寻她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个人与社会责任之间找到独特的平衡点。
ManGu:Capa Dara Resort在2012年成立,当时你还在求学阶段。那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后会从事酒店管理这一行?
Beau Pattamon女士: 并不是,小时候想长大了去外国生活。我在芭提雅长大的,当时觉得很想去外面看看世界,11岁的时候就和家里人要求去参加新西兰夏令营,特别想尝试一个人生活。我爸爸说我4、5就会自己收拾行李说“我要去马来西亚”了,而且是和他们打个招呼的感觉,不是问可以不可以。后来,因为觉得泰国的传统教育不是很适合自己,像数学、语言之类的都不是自己擅长的科目,爸爸就去帮我看了澳洲的学校,那里的环境、氛围都不错,到澳洲学习酒店管理了。澳洲的高中会提供职业相关的科目,比如酒店管理、商业管理和经济学等,对以后走入社会更有帮助。在澳洲留学的经历让我从小培养起来自律与独立,我在生活和学习中都受益匪浅。后来选择回到大学继续深造旅游与酒店管理,也因成长环境的熏陶,使我能够更快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并在实际应用中具备较强的适应力与胜任力。
 ManGu:澳洲的高中已经开始学习这样的科目了吗?
ManGu:澳洲的高中已经开始学习这样的科目了吗?
是的。澳洲的高中会提供职业相关的科目,比如酒店管理、商业管理和经济学等,高中就学到了一些将来真正能用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去澳洲真的很值得。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放学后要做哪些事情,才能保证晚上 11 点前入睡?因为如果睡得更晚,第二天早上就会很累。比如去超市买菜、做饭、做作业……虽然那时候和朋友住在一起,但我也尽量自己照顾自己。这些技能对我来说终生受益。之后回来玛希隆大学国际学院学习旅游和酒店管理,可能因为家里原本在经营酒店,相当于我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所以在学习的时候所有的知识都接受得很快,就像如果真的要我去参与酒店管理我也完全可以胜任。
ManGu:家里本来就在经营酒店是吗?
Mike Group 是芭堤雅的第一家商场,下层为 Mike 百货公司,上层则是酒店,形成了商场与酒店结合的复合业态。这种模式在香港早已普遍,上层为酒店、下层为百货,业态完整而便利。可能正因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们家族的孩子们后来都选择了与酒店管理相关的职业,并大多沿用了家族的酒店名称。然而,当时由于名称过于相似,也引发了一些困扰。许多客人到达后会说「不是这家」,司机也常常分不清目的地。我们原本以为统一的命名能让品牌更具整体性,但在当时社交媒体尚未发达的环境下,客人反而难以分辨各家酒店。于是,父亲决定在 Central Pattaya 附近兴建一间新酒店,并命名为 Baron Beach Hotel——这是第一家没有沿用「Mike」名字的酒店。随着运营,这家酒店逐渐展现出新的特色。后来,我们也陆续发展了公寓等多种业态,并逐渐采用新的命名方式。有一次,父亲来到这里,他说这片地方让他想起了童年与家人从曼谷到芭堤雅旅行的幸福时光。因此,他希望能将这里打造成「所有家庭的幸福之地」。那个年代的芭堤雅与今日截然不同,很多人来此更关注购物。但当酒店落成后,客人们纷纷表示惊讶:「没想到这里竟然是芭堤雅!」、「这和我印象中的完全不同!」、「原来芭堤雅的海滩如此美丽!」
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我自己也在海边长大,但过去的海水与沙滩并不干净。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悉心养护,如今的沙滩才呈现出如此洁净迷人的风貌。酒店地处悬崖旁,从大堂步行至沙滩,景致开阔,风光尤为特别。许多客人都认为,这里的第一印象非常适合休憩与放松。

不少娱乐圈人士也曾在此寻得慰藉。例如演员 Dai Diana,在 COVID-19 期间因承担公益工作而失眠。她初来酒店的第一晚依旧难以入眠,但第二晚,她坐在窗前,从夜晚九点一直看着景色到次日清晨。她感受到大自然的清澈生机,听着鸡鸣声与晨光一同苏醒,心境豁然开朗。她告诉我,那一刻她突然明白,生命就是如此循环,而她已经尽了全力。当晚,她终于睡得像个婴儿般安稳。我听后非常欣慰,也由衷感到我们的酒店真的能够给予人力量。
在酒店规划之初,家人希望同时满足情侣与家庭的需求。但我本身学习过市场营销,我认为必须要明确目标。然而,当酒店真正投入运营后,我发现最终还是由顾客来定义产品。事实证明,不论是蜜月情侣、退休夫妇,还是休闲度假的家庭,都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美好体验。不过,酒店开业的第一年并不轻松。账单一张接一张地堆在我父亲桌上,让人焦虑万分。我希望能尽快让酒店打响名气,于是翻开手机通讯录,寻找能提供帮助的人。偶然的机会,一位博主朋友帮忙联系到影视剧组,最终吸引了十余部作品在此取景拍摄,酒店逐渐获得了关注。之后,我们又尝试与合作银行、杂志展开联动宣传,从零开始学习宣传与公关,逐步累积经验。到第二、三年时,酒店终于走上正轨,宣传带来了百万级销售额,也逐渐成为市场上的热销酒店。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做事必须具备前瞻性。尤其在 COVID-19 期间,所有人都困在家中,旅游陷入停滞。那时,我们家族的兄弟姐妹分别毕业于不同大学,我便建议大家在各自的校友群里推广酒店预订链接。甚至父亲也亲自参与,在校友群里活跃宣传,他的群名还是「Beau 很想念大家,来找她吧」。这种方式意外地带来了成效。同时,我也在一次代购群里得到灵感。那个群里的商品瞬间售罄,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种即时互动的营销方式。于是,我为酒店开设了open chat,邀请粉丝加入互动。事实证明,这个举措收获了极大回报。正是在那段关键时期,我真正体会到信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传播,而企业也必须随时根据环境灵活调整思路。
 ManGu:您在一开始就参与了这所酒店的规划、建设和推广是么?
ManGu:您在一开始就参与了这所酒店的规划、建设和推广是么?
是的,我当时还没有毕业,在玛希隆读大三。我一般是周五下课后就开车回来开会,周末在家,周日再回学校那边。我穿着大学的校服,看起来好像很不可靠,很小没什么工作经验,说什么大家都会偷偷地笑,即使我在家里是最大的女孩,上面是一个哥哥,兄弟姐妹有5个人。但其实我是会议桌上唯一一个酒店管理专业的,一边学一边就学以致用了。开玩笑说,我遇到不懂的还能随手掏出手机给老师打电话,这里还没教呢,老师您先给我点建议,等下老师会回我“先冷静”。像各类型的房间,客房和洗衣间这些应该如何设置,我都会根据我学过的内容有个大概的想法。还有设计方可能不太清楚一个办公室得有几个卡座之类的,但我就心中有数,可以给工程人员提供意见,比如这个部门位置要宽一点,另一个部门就可以紧凑些,因为结合我学过的知识,我会知道这些部门大概有几个工作人员,比如5个职位,有5个人,但如果有人兼任多职,实际可能只有3个人,全都根据真实情况来设置。
ManGu:毕业后您就到家里的酒店来帮忙了是吗?
没有,我认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十分重要,如果我到家里的酒店去,那里的人会觉得我是老板的孩子,不敢教我,所以我向家里人提出先到别的酒店工作1年,虽然也是在芭提雅,因为不想离家里太远。那个时候刚好有个朋友想来这里开旅馆,他邀请我加入,我问他我适合什么职位,他说我可以兼任销售和市场营销。虽然一个人担任两个职位看起来有点不可能,但我还是接受了,我觉得他既然觉得我可以,那我就可以。真正开始工作后发现其实我身兼五职,任何干得来的都干,不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课。那時候总经理說因為我在芭堤雅長大,熟悉芭堤雅,指派我去规划這酒店一年的計劃。大约一年后,芭提雅的这个酒店快开业了,我想趁这段时间再去学点别的,就和爸爸说我想去学時尚设计。然而,我申请的商科研究生全通过了,设计类的一个都没通过,所以我就去了外国读设计类的短期课程,大约6个月后再重新回来进入这个酒店工作。

ManGu:之后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有很多,一开始就已经不容易了,开分店也不容易,我记得我当时累到回家直接躺地板上睡着了。为了帮酒店打开名声,公关、剧组、杂志之类都邀请来酒店,看到酒店出现在知名杂志封面时其实我内心是无比骄傲的。第二个大困难时期是俄罗斯经济下行,导致很多游客都不来了,那个时候也让我意识到我们应该出去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推广酒店,像日本、英国,我们都去路演,去认识我们的合作伙伴。爸爸那个时候和我说,他给我的月薪一辈子都不会变,所以如果我需要更多就必须自己去挣。可是我7*24小时都在这里了,我还能怎么扩展呢?后来我想到,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娱乐圈明星、生意伙伴,我可以把他们变成客户,把酒店品牌宣传出去。爸爸也认同我这个想法,所以我开始把这个酒店扩展到多位置、多类型,一路通关直到我的孩子到来。接着就是COVID-19时期了,那时就像一个长长的假期,我在海边散步的时候会有“感谢我们还活着”的感想,觉得自己十分的幸运。有时候醒来看到海边等着拿物资的长队,会突然伤感,会思考很多人生问题,比如为什么有人可以一直剥削他人。再后来我自己就想通了,这可能是因为人心不足,所以我又开始想我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个情况吗,比如我们为下一代建设一个富足的环境,让他们学会知足,这样可行吗?我不断地思考,一遍又一遍,或许我们可以教会他们“爱”。小孩子会以自我为中心,借此保护自己,如果周围的人给他们足够的爱,他们再去看待其他的事物时,他们也会想爱其他人和物。这个想法促使我想去先充实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去给予他人,而且我想如果我们这么做,下下一代就会有所改变。加上当时有不少人陷入抑郁,我看着我女儿的时候也会想,我该做什么让你能保持乐观、自信呢,这样你长大后就能有无限的潜力。最终,我决定开一所学校。我再次去咨询了我的爸爸,这个决定很重要,因为我在学校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都非常少,所以我想问问他的意见。
ManGu:之后您就决定开办学校,这段时间的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我是单身妈妈,这让我更坚定要为女儿创造最好的成长环境。疫情期间我读了许多心理学书籍,其中一本提到,人的幸福感有70%–80%来自人际关系。好的关系让人长寿、快乐、成功,也赋予人自我修复的能力。这让我思考如何为孩子们营造这样的环境。最初我考虑与成熟机构合作,在一次聚餐中朋友提到一个有相关经验的团队,我便联系上他们。视察时我问“能保留所有的树吗?”得到肯定答复,那一刻我仿佛觉得命运眷顾了我。很快合作达成,还遇到了一位愿意加入的教育专业人士。最终我们选择了英国课程,因为它能帮助不同背景的孩子因材施教,避免过度分层,同时具备全球适用性。在教育方法上,我研究了蒙台梭利、瑞吉欧、华德福等体系。女儿在疫情期间我也用过蒙台梭利,但后来我选择了瑞吉欧。它强调协作和领导,尤其适合帮助孩子重新适应社交。瑞吉欧理念中,老师是“引导者”,教育应源于孩子的好奇。比如母鸡下蛋,老师会顺势引导孩子探索知识。教育的本质是有目的的“玩”。
在师生比例上,我们保持平均1:2.5,这让老师更容易发现并帮助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曾有一位中国学生,敏感、自卑,不愿接受自己的名字,还带有攻击性。老师陪伴他整整一个小时,被打也不离开,最终获得了他的信任。我们相信孩子的不良行为并非故意,而是他们在以感官方式探索世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过敏原”,有的怕强光,有的怕噪音,有的需要触觉安抚。了解这些,就能帮助他们找到安全感。
因此,我在招聘老师时尤其重视他们是否真正理解教育,能否在被激怒时保持温和。老师不仅是知识传递者,更是“魔法师”。他们会通过细节示范引导孩子,比如在打闹时展示正确的相处方式。我们的教育理念也融入“可持续”。女儿在学校不仅学习垃圾分类,还通过Coco Chanel、西太后等品牌的案例理解设计与循环再造的概念。这样的教育让孩子们拥有能力,同时保持快乐与坚强。我坚信,这种方式能够塑造幸福、自信、有爱的下一代。
.webp)
.webp)
.webp)
.webp)
.webp)
.webp)
ManGu:现在的大人其实也有崩溃的时候,对吗?
是的,因为很多大人在小时候没有人教他们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像我小时候一哭,大人就说“别哭别哭”,我说“疼”,他们就说“不疼不疼”,这其实是一种把情绪推出去的方式,而不是化解,这样长久下去人就会感到压抑,所以我很庆幸我在我的孩子长大前意识到这点。
ManGu:所以现在您的工作重心是在学校这边,不是酒店管理了是吗?
重心是在学校这边,但酒店的事务也有在关注,像近期中国游客减少,我也会和酒店的管理层一起想推销方案,两边其实都需要参与。一般早上起来把孩子送到学校,我的工作也开始了,直到放学,酒店那边,比如会议什么的,就穿插在学校事务中间的空闲时间。不过还好,现在我的哥哥、妹妹、弟弟都来帮忙照看酒店,所以我在酒店那边主要是和品牌管理和销售这方面的工作,其他他们能够处理的就放手给他们自己决定。
ManGu:您也是华裔对吗?
是的,我的爷爷是海南人,奶奶祖上是潮州人,不过我爸爸是在泰国出生的,我妈妈则是完完全全的泰国人。所以我是50%的华人。

ManGu:成长过程有接触到“华裔传统”吗?
至于家里的“华裔传统”是和吃饭有关的,一粒米都不能剩下,不然家里会说“等下爷爷看到了会生气的”,因为爷爷觉得挣钱不易,粮食也得之不易,不可以浪费。我的爷爷奶奶出身都不富裕,爷爷是裁缝之类的工作,而我可以说是跟着奶奶长大的,我和她睡一个房间直到我大学毕业,甚至可以说奶奶是我的另外一个“妈妈”。我和奶奶外出的时候,如果我抱怨什么,比如说“怎么路这么堵”,奶奶就会和我说“只有你有车吗?大家都堵着”,她在教我不要觉得自己有“特权”。因为我在酒店长大,一切都有人安排好,奶奶的提醒就像把我拉回到地面上,脚踏实地,包括开酒店时也一样,奶奶告诉我,做生意不要只想着自己富,要让大家都挣钱,大家一起成长。我从小就看奶奶捐赠红十字会,她做这些并不是为了得到回报,而是让我们自己觉得安心,像有人来求助,她也不是“好的好的”说完就忘,而是能帮就直接帮了,之后也不会一直记着说自己帮过谁。除此之外,家里还保留着传统的华裔祭拜仪式,像春节,家里的贡品得有一百份吧?我记得家里的客厅,这边好多好多篮橘子,那边好多好多篮苹果,全都堆满了,大家都要帮忙一起布置,而且要祭拜的神也很多,这位也拜拜,那位也拜拜,还要注意这里先那边后,不然这里会过热,一整个仪式完成后,大家都好累。
ManGu:那您有学过中文吗?
有的,非常有趣。我家里人其实说泰语为主,但我有听过奶奶和姐姐说过潮州话,我一句都不懂。后来爸爸说,中文非常重要,如果会说中文能帮助我们了解世界,所以在玛希隆读大学时,我选了中文作为第三语言。不过当我学到level 2时觉得实在太难了,我就休息了1年左右,结果重新回来学的时候发现全忘光了。为了不挂科我就到北京又学了1个月,再回来继续学习,虽然我当时只是B+,但还是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我可能写的能力不行,拼音和字这些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日常对话我大概能理解。
ManGu:您会教您的孩子一些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吗?
会的,学校就有教中文。我记得有一次,她回来问我“妈妈,我们是有钱人吗”,当时我不确定告诉她和金钱、阶级有关的内容会不会不太合适。后来,我把我在COVID-19时期整理的奶奶的故事拿出来讲给她听,奶奶是怎样一步一步,从什么都没有,到取得了很多成就的。还有传统的祭拜仪式,她也会参加。对于我来说,把很多件事情安排妥当是比较重要的,现在一切已经步入正轨,所以我都可以兼顾过来了。
ManGu:芭提雅的华人多吗?
很多,大概6成、7成本地人是,现在他们大多数在做生意。

ManGu:您的日常生活大概是怎样的?看起来好像工作和生活已经成为一体。
是的,基本上每一个采访都会这么说。因为我生活在酒店这里,工作也在这里,但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我其实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所以并不像其他人会把工作和生活分的很清楚。如果我想休息,我就回曼谷的家里,那里没有工作人员,我可以看Netflix,喊Grab外送,干什么都行,就像度假。COVID-19过后我回曼谷的家里,大概离上次回去一年多,我那个时候感觉我只是需要个私人的地方,因为平时我的家就在酒店在商场里,都是我的工作场所,穿衣服也需要注意,不可以穿短裤,不可以穿拖鞋。
ManGu:那您的空闲活動是怎么定义的?
和朋友聚会吧。我认为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朋友,他们是我们的力量之一。平时工作会消耗能量,但当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开玩笑的时,感觉能量又回来了,又可以去战斗了,累了又约约朋友出来吃饭聊天。还有,我喜欢普拉提,普拉提和瑜伽不太一样,在做普拉提的时候必须全神贯注,不然会有点危险,所以那一个小时里,我的大脑完全脱离了工作,肌肉也得到了锻炼。


ManGu:最后,您有什么想和我们的读者说的吗?
《曼谷杂志》是一本中文杂志,我想借它和中国的朋友说,芭提雅现在依然非常美丽、安全,可以放心来旅游。我在泰国生活,我知道泰国绝大部分地方都是有安全保障的,曼谷、芭提雅还有其他旅游热门地都很安全。另外,我创办的学校Lovell是一所国际学校,现在有来自非常多国家的孩子在这里就读,几乎20个孩子20个国家,有一些是混血儿,他们的家长在母国也取得不错的成就,但所有的家长都有同样的看法,世界本质上是个地球村,他们在哪里工作都可以,也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妈妈们,她们都追求高品质生活。每次和他们交谈,我都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选择送他们的孩子来这里读书,他们敢于走出去,接触未知,他们的孩子以后心态也会非常健康。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也是我的愿望,所以如果大家和我想法相同,也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学校来。